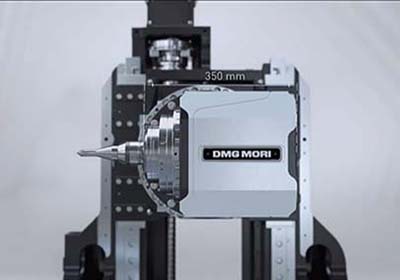宣传片制作
当导演一定要具备的思维
当导演一定要具备的思维
在初读剧本时,有三个关键问题会浮现出来:
1.类型或曰故事形式是什么?每个故事形式都有不同的戏剧构架、人物呈现和情节设置。
2.谁是主要人物,其目标是什么?应该有一个目标明确、鲜明独特的主要人物。
3.人物弧线是什么,或者换言之,在故事中的经历会如何改变主要人物?你应该能够判定人物在故事开始时的状态,并明白随着故事的展开人物将如何变化。
在重读剧本时,应该回答另一组问题:
1.故事的前提(premise)是什么?故事的前提——有时被称为主干、主要冲突或驱动——最好是主要人物面临着两个对立的选择。这两个选择往往与叙事中呈现的重要关系有关。
2.前提与主要人物及其目标是否一致?应该一致。举个例子,如果《大审判》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成功的律师,那么为浪荡生活重赋尊严的前提就不会引起共鸣。前提与主要人物之间必须具备关联。
3.主要人物的转变是否可信、有意义、在情感上令人满足?
4.影片中的情节是什么,被应用得如何?从理想状态来说,当情节里嵌入与主要人物目标背道而驰的力量时,情节才能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漫长的婚约》(A Very Long Engagement,2004)中,一个年轻女人无法相信她的未婚夫在“一战”中遇难了。战争的毁灭性,以及找到他破镜重圆的情节,似乎更近于幻想而非真实的可能性。除非情节在主要人物实现目标的道路上设置某种障碍,否则情节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再想想《泰坦尼克号》中那艘巨轮的航行,那是令情节卓有成效的典范。轮船沉没了,罗丝的爱情变成了回忆而非现实。在故事中设置情节可能是导演的短板,因此需要在这一方面下足功夫。
5.如何让代表前提那两个选择的次要人物与前提契合无间?他们是不是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帮助者与伤害者?某一个帮助者比其他人更加重要吗?何以如此?反派会是所有人物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着主要人物反应的强弱、人物弧线的轨迹,以及我们在影片结尾对于主要人物的感受。反派越强大,我们主要人物最终予人的感觉越像英雄。就其本质与动作而言,次要人物在剧本中起着特别的作用。他们的谐振越是贴近真人而非简单的故事元素,剧本就越丰富。尽管我们是通过主要人物来经历故事,次要人物却可以帮助剧本显得更加可信,更加引人入胜。
在此让我们回到类型这一问题上来。类型暗示着影片的戏剧弧线。惊悚片是追逐;警察故事讲的是破案,把罪犯绳之以法;黑帮片讲的是主要人物的沉浮兴衰;科幻片探讨的是技术对于人类的威胁。有些类型的侧重点是内心。情节剧是围绕着丧失、野心或精神重生的内心旅程而展开。情景喜剧关乎生活中的价值观和主要人物的举动(比如,在《窈窕淑男》中,一个男人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在事业上的雄心而假扮女人)。
山东片也倾向于谈论价值观,代表着正面力量的田园牧歌式的渺不可追的过往,以及代表着负面力量的文明和进步。每一类型都有不同的形态。什么是戏剧弧线?它怎样服务于主要人物的目标?如果剧本没有亦步亦趋地符合类型期待,那么这些变化是令剧本更好,更新鲜,更有力度……还是相反呢?既然你已经读过两次剧本,做了丰富详实的笔记,下面就该三读剧本了。为了探索能够催生导演思维的剧本维度,三读剧本是必不可少的。
走向阐释
请把这一回合设想为文本阐释的应用。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下面提及的维度中揣摩故事的潜在可能性:
生存的维度
心理的维度
社会的维度
政治的维度
每一维度都会编织出不同的故事。
让我们看看《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2003)。在政治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影片具备日美关系的维度。像比利·怀尔德的《玉女风流》这样的影片是把政治与政治分歧推上了前台,但是在《迷失东京》中,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似乎对于故事的政治维度兴趣寥寥。《迷失东京》的社会维度又如何呢?在此有没有阶级或性别问题的介入?有没有等级制度,一个群体压迫另一个群体?也谈不上。本片的社会学读解在索菲亚·科波拉看来并不重要。
《迷失东京》的心理维度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不是一个涉及不幸或者其他性格问题的故事呢?两个主要人物的不幸可否在起因和疗治的范畴中界定呢?不可以。那么,让我们看看生存的维度。两个主要人物,一位演员和一个年轻摄影师的妻子,都拥有貌似完满、实则孤单的生活。他们与配偶的对话提醒了我们,他们在这个重要的关系中感觉是多么孤独。置身于一个社会习俗别具一格的奇怪的异国文化之中,并没有缓解两人的困境。只有彼此的友谊使这两个人物免于彻底的孤单。索菲亚·科波拉把文本阐释的重心落在了生存维度之上。她本可以选择其他任何一个维度的——心理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然而,不同解读方式的取舍,会让影片彻底改观。
导演在发展导演思维时可用的第二个棱镜是叙事与当下议题之间可能搭建的关系。每一个时间段都有自己时代一望可知的议题。比如,看看2005年,彼时的大议题包括宗教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全球化、环境挑战、隐私权、平等(比如,在男性世界中女性的权利),以及,当然,现代主义与传统之争。还有许多其他特有的、本土的议题,但是对这些大议题,应该在更加迫切的个人、民族和国际层面予以关注。
如果导演对于社会充满激情,时代议题就是解读剧本的一个棱镜,与剧本息息相关。这些议题也给了导演一个平台,来表达他或她的个人信仰,或者给了导演一个工具,来吸引观众。时代议题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落实在导演思维上。史蒂文·索德伯格经常借用时代议题让自己的叙事更加引人关注。权力及其搭档——腐败——驱动着《毒品网络》这个有关毒品的故事。索德伯格的复仇故事《菩提树下》的核心则是父母之道。在文本阐释中考虑时代议题有助于拓展导演思维。
能够传达导演的观念的声音表达,则是另一个手段,推动导演从文本阐释走向导演思维。声音可以很充分地反映导演的性格。斯坦利·库布里克对于人类进步的看法是野心勃勃的、反讽的、充满激情的。技术或科学观点认定人类在不断进步,库布里克却不以为然。科恩兄弟也秉持着库布里克式的怀疑主义,但是他们在就此陈述看法时,态度要戏谑得多。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于这一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但是态度更为乐观,他的叙事,与库布里克相比,更加正面,充满希望。《人工智能》本是库布里克的项目,但是在库布里克身故之后,由斯皮尔伯格接手执导,从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呈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的冲突。库布里克完成的剧本透出了他的批评之声,但是视觉风格和表演则反映了斯皮尔伯格较为乐观的立场。
有些导演对于声音的问题认识得很清楚,对于他们来说,观点的传达要优先于戏剧考量。他们会选择以声音为取向的故事形式——特别是讽刺剧、历史剧、寓言和非线性的故事。这些类型无一例外,均运用了保持距离的策略,比如反讽,以免我们与主要人物产生认同和情感代入。其结构也有助于我们与主要人物保持距离。观众在观看时不会与人物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导演与观众的关系更为直接,因为没有观众与主要人物的情感关系介入其中。声音表达是用来发展导演思维的最直接的工具。
说导演思维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不包含宣传营销的考虑,未免太不诚实了。除了声音之外,在发展导演思维的过程中,宣传营销是导演最上心、最深思熟虑的考量。对于导演来说,这可能是单一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轰动意味着票房。轰动可以由情节、性的潜文本、暴力的潜文本,或者夸张的基调或风格来制造。在昆汀·塔伦蒂诺(《杀死比尔》[Kill Bill,2003])、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戏梦巴黎》[The Dreamers,2003])、吴宇森(《碟中谍2》[Mission Impossible II,2000])和阿德里安·莱恩(《致命的诱惑》[Fatal Attraction,1987])的作品中,癫狂无度和商业主义历来如影随形。在导演思维的发展中,宣传营销是一个强大的形塑力量。
选择导演思维
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剧本分析,确定了是故事的哪一方面引你入内,现在你有五个选择来构建导演思维。每一个选择都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聚焦于以下几点之一:
1.人物弧线——以主要人物及其转变为工具。
2.戏剧弧线——情节是驱动力。主要人物与反派的斗争决定了戏剧弧线的走向和形态。
3.潜文本理念——叙事可以平铺直叙(比如《亚瑟王》的浪漫的高贵),也可以繁复纠缠(比如《沉默的羔羊》)。在凸显潜文本的过程中,人物弧线和戏剧弧线都被纳入了潜文本。
4.声音——举例来说,涉及战争(比如,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家庭价值观(比如,科恩兄弟的《抚养亚利桑纳》)或者民族侧影(比如霍兰的《欧罗巴,欧罗巴》[Europa Europa,1990])的导演思维,会主宰叙事结构。
5.你生命中最深层的价值观——有些导演的精神个性是在其切入叙事的手法中揭示出来的,比如:让·雷诺阿(Jean Renoir)影片中的人道主义;伊利亚·卡赞对于阶级、种族和代际差异的不无争议的构建;罗曼·波兰斯基探索生存之孤独的视界;以及谢尔盖·爱森斯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一旦你的导演思维被界定,你需要把指导演员的手法概念化,把切合你的导演思维的摄影策略也概念化。记住,你的手法越是多层次,就越有创造性,同时也要甘冒一定的商业风险。